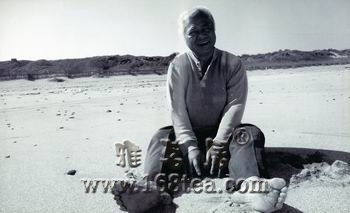
胡德夫生平
1950年,出生。11岁前,台东大武山下放牛的小孩。
1962~1968年,12岁从台东部落到台北淡江中学读书,原因是父亲认为淡水离日本比较近。在教会中以唱圣诗被启蒙。
1968~1970年,18岁进入台湾大学外文系就读,后因长期打橄榄球造成运动伤害,中途休学,开始崇尚并传唱Bob Dylan等西方歌手的自由与反战歌曲。
1972~1976年,21岁开始与李双泽等人推动“唱自己的歌”运动,开始使命为社会与族群创作歌曲,影响致后来台湾全面的“校园民歌运动”。
1982年,在族群意识鞭策之下,开始推动“党外编联会少数民族委员会”,任召集人,并以创作控诉社会对自己原住民族的不平等对待之歌曲。
1984年,领导创立“台湾原住民权利促进会”,任一二届会长,并强力主张社会不能再以“山地人”、“山胞”来称谓自己的民族,并统一其称谓为“原住民族”。
1990年,返回部落与阿美族耆老郭英男等音乐家学习生活,沉潜数年,从太平洋的风声与海浪声中体悟自己土地的音律,并重新学习部落歌谣。
1997~2000年,于“原住民族部落工作队”以部落服务与传唱作为个人的重新出发,期间台湾发生的九二一大地震之后,致力于救灾、请命及创作歌曲。
2002年始,于“野火乐集”原住民音乐团队,将部落的声音与世界音乐结合,开始为部落做以声音呼唤的工作,带领新一代原住民歌手创作与激荡歌谣,矢志让“用力敲钟,大声说话”的灵魂不死!!! (由野火乐集提供)
《匆匆》录制日记
记录者:陈冠宇,好客乐队团长。《匆匆》录音、混音工程师。
记录者:陈永龙,卑南族歌手,擅长沙铃、合音与手鼓。《匆匆》制作助理。
2004年5月
虽然经过保养,但这钢琴仍然看得出来,历经风霜。仔细端详,发现甚至断了一根弦。一个黝黑的壮硕男子,稳稳地坐上钢琴椅,从小在野外锻炼而得的布满厚茧的手指碰触琴键,传出来的却是温暖轻柔的音符。“在那往日的树林里,落叶依然满园……”他缓缓唱出《枫叶》,厚实的嗓音略带沙哑,与钢琴声一同回荡在这有半世纪历史的教堂中。录音座前的我,愣住了,被层层叠叠的悠扬乐音包围。
“这首歌是念书时候写的,用这台钢琴写的曲,写给我暗恋的那个女孩。那时候就在这里唱,希望那女孩能够听到”。《枫叶》这首歌一唱完,Kimbo就对我们几位朋友说明这首歌的来历。我突然懂了,这座小教堂,就是最适合Kimbo表达自己情绪,最适合他录下数十年来作品的场地。
2004年7月1日
淡江中学的小礼拜堂,阳光会经由彩绘玻璃透进来,木头的古老窗子打开时会发出吱吱的声音,平台钢琴的琴声会充斥整个空间。加上窗外的蝉鸣,树叶被风吹动的声音,还有胡老师的琴声,歌声,竟是合而为一的……专辑中若出现了蝉叫声或雨声……一定是我们精心安排的。
2004年7月5日
“人生啊就像一条路,一会儿西一会儿东……匆匆,匆匆”大雨就在钢琴的尾音时急速落下,就像它也在静静地聆听胡老师的匆匆,然后听完,大声鼓掌……很少有机会这么接近平台钢琴,手弹到琴键会清楚的看到它打到琴弦,就会有种跳跃的生命是人给予琴生命,还是它本身就有?断了两根弦的钢琴,其实是可以把它修复到更完美,但我们决定保有它的缺点,就像人,都有自己独立的特质。当然琴也是。
2004年7月9日
准备搭捷运的路上,接到了捷任(注:《匆匆》制作人)的电话,说老师今天有些状况,今天可能无法到淡水录音。是什么重要的事呢?我立刻打了电话给胡老师询问是啥状况。老师说他从前一天晚上就一直在联络直升机的事情,要送粮食到仁爱乡给居民,目前仍在持续联络中,也号召了他企业界的友人,准备了约200公斤的粮食,要一早送到部落。然后他找了捷任要陪他一道前往灾区……老师的音乐有山,有海,有人民,今天他虽然没有坐在钢琴前唱歌,但,我却清楚听到了他的音乐……
2004年8月4日
最后一天,我们依照所排定的工作时间表,开始这最后一天……
小礼拜堂的钢琴,依旧走了几个音,每天都急电苏姓调音师赶来淡水,帮我们救救这台总是要走几个音的钢琴。调音师骑着他的摩托车,终于急忙忙地抵达,开始他一个音一个音的调弦工作。
午后阳光洒落,调音师就这样趴在钢琴上调音,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调音过程!他就拿出棍子般的调音器,一个音一个音的判断,哪根弦松落了,仔细地听着每个音的间隔。调音是件需要严谨态度面对的事情,调音师整整调了两个小时。但我们也没闲着,因为操场上正展开一场激烈的橄榄球赛,橘色球衣对蓝色球衣,在50码的地方排起阵势,肩负达阵任务的球员,一路向前跑着,不时闪躲着敌队的拦阻,一路向前冲着。一旁帮忙解说球场规则的胡德夫,想起早年在校园也是如此挥洒着青春的汗水,跃跃欲试的神情从他的眼睛悄悄地泄漏出来。我想,在那些你来我往的球赛中,说不定,胡德夫年轻的身影正在场上跑着……
2004年8月热天
某日“来来来!给你听听看!”我边说边将耳机递给走向我的Kimbo透过耳机,他听到刚才弹唱的两首歌,低着头,他听得非常专心仔细。音乐结束,抬起头,他问我:“唱得可以吗?好像还不行呢……” 身为一个录音师,又同时是个乐团主唱的我,对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熟悉了。其实刚才录下的曲子,令我非常悸动。是非常真诚撩人的表现。那个沉浸在乐音发生当下放嗓高歌的Kimbo,是多么的充满自信!但演奏完毕走向我的那个Kimbo,虽然带着微笑,却又掩不住他的害羞与不确定 。我不带怀疑地递过录音师专用的耳机给他,就是试着缓和他对自己的怀疑,告诉他,我刚才真的很感动! 在录音的过程里,被麦克风指着的人,演奏演唱的音乐人,经常会产生这种情绪。这状况常常源自求好心切的焦虑感。而录音的时候,因为现场布置了大批器材,大伙工作时那种“就是要工作、就是要录音”的专注,很容易造成一种对立的气氛,一种台上对台下、演出者对观众、被录音者对录音师、音乐家对制作人的对立。这种对立的气氛往往更加重了那种焦虑感,而一发不可收拾。由于演奏演唱者的情绪很容易就显露在音乐表现中,所以若不好好解决这种对立气氛与焦虑感,那录制出来的成品,常常会很生涩紧绷。很多自我要求非常高,但又不懂这些心理机转的制作人,常常会把作品搞砸,这就是原因之一。幸运地,在Kimbo这个录音专案中,我们选择了在这间礼拜堂录音。这里没有一般录音室分隔录音工作者与被录音者的那种很像在动物园里“观赏企鹅游泳”的双层玻璃。大家都身处同一个空间,聆听着整个空间的自然余音回荡。制作人郑捷任甚至就坐在Kimbo的钢琴旁,随时与Kimbo聊天互动递水递点心。而Kimbo若兴起,随时可以起身走向十排座位外的我,透过我的耳机,仔细聆听他的杰作。还有一点,一般录音室绝对做不到的:礼拜堂外就是个小型足球场!录音录倦了,拎起足球,几个人就叫着喊着往足球草地上冲。长传、射门、守门、高吊角球,甚至连鞋都不穿。透过身体的激烈活动,透过沁出的汗水,来放松焦虑紧绷的头脑,这应该是现代的音乐人很少享受到的幸福吧!
2005年1月28日
这些是 Kimbo 的混音Audio CD,今天下午终于将它从96K 24bit的源文件烧录出来。当我检查这些音轨,这张CD,我突然觉得我好像在酿酒。从录音前的构思录音场地、录音器材计划到夏日艳阳雷雨中的挥汗录音以及费时3日的选歌辩论、而后进行大量素材的长时间混音,最后烧录出了这张CD,就像”夏子的酒”故事里,整仓的稻米经过研磨发酵,最后榨出的一瓶瓶清酒。当然,对Kimbo 而言,这过程更长,是生命去撞击累积、历史深邃的沉淀、社会剧烈变迁的历练而得,用这区区三言两语根本道不尽。我很荣幸能成为这大吟酿的第一个品尝者,并希望这些录音作品也热起每一位听者的心胸。





